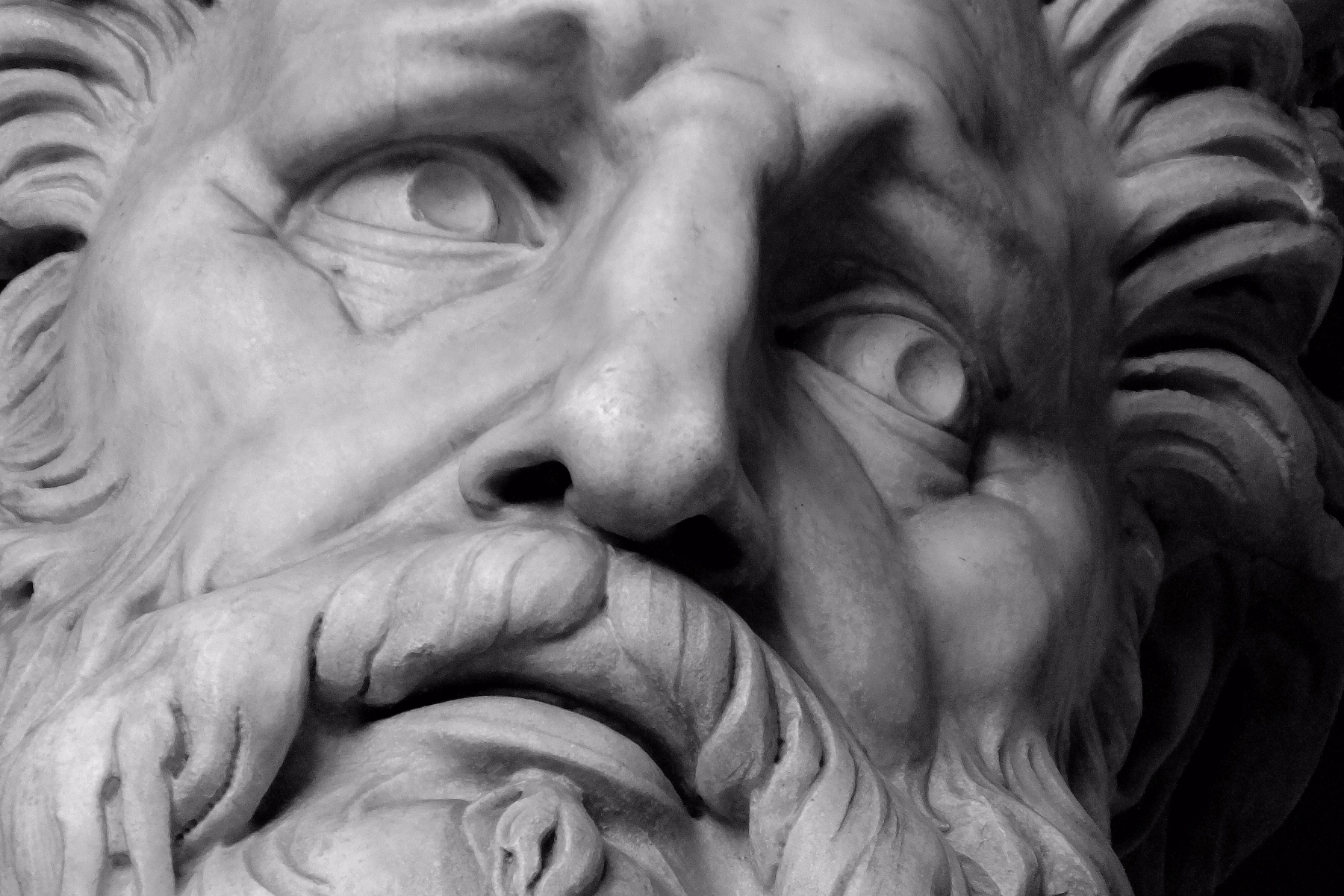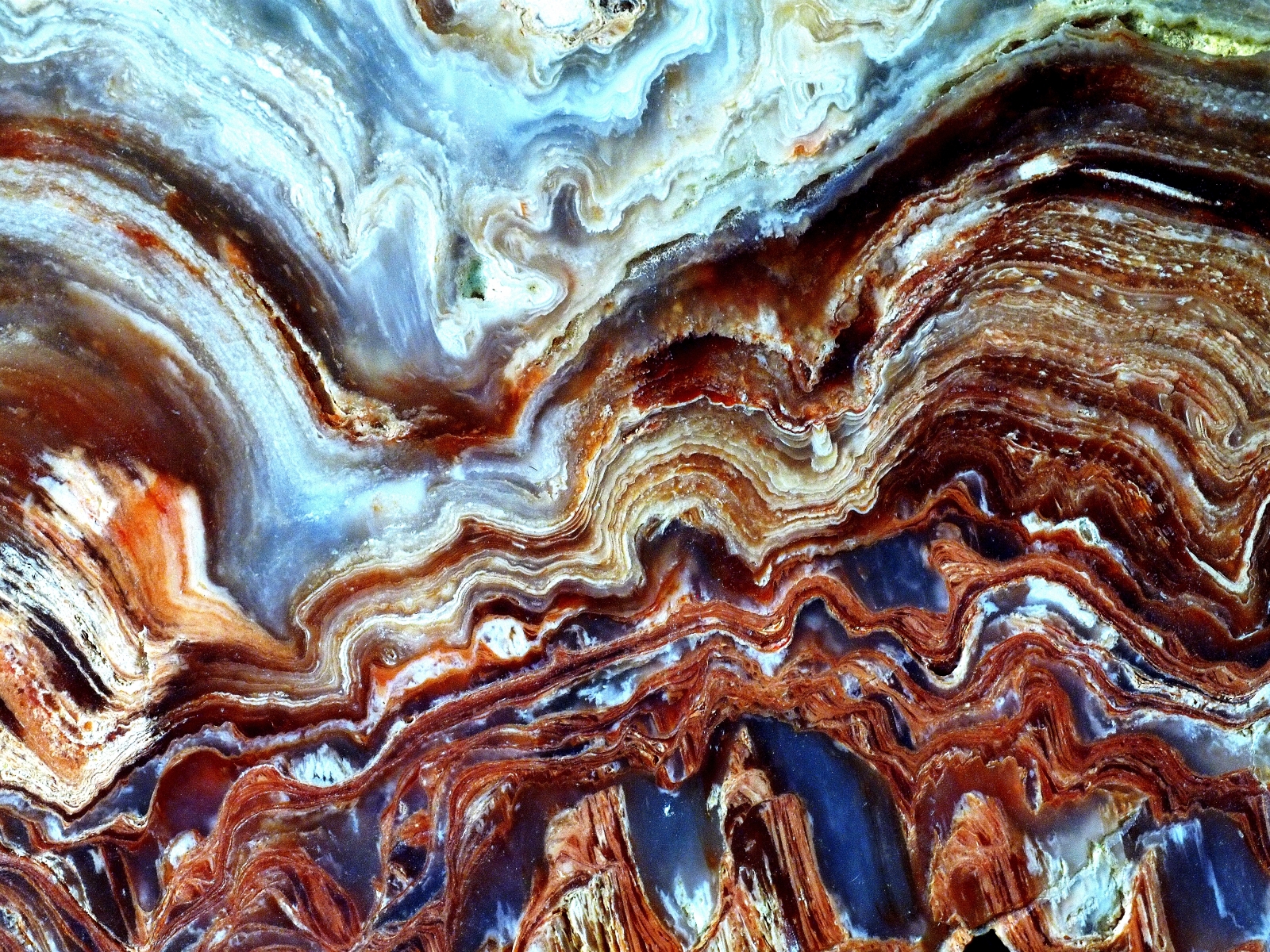纪念陈一咨
“陈一谘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括号,二十五年前退出了,括号完。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人名的抗日战争,括号,抵抗被政权强奸的命运的战争,又叫改革,括号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括号,“不远万里”是指他与万里和紫阳套近乎,“来到中国”应改为被迫离开中国,括号完…”
爱说段子的老陈,若听到上面的悼词,会不会乐得醒过来?那个年代的人都对老三篇倒不背如流,把为人民洗脑的《纪念白求恩》改成《纪念陈一咨》,老陈一定接受这点幽默。
老陈走了。虽然熟知他的病情,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消息传来,还是陷入一阵长长的静默无语。洪朝辉老弟来信说要编个纪念文集。虽然手头欠着一堆工作积压,还是立即答应了写一点。
第一次见老陈,是在木樨地22号楼,何维凌家中。刚从北京站下火车的我,风尘仆仆跳上地铁直奔老何家,那是我的“京城联络站”,也是80年代初全国众多的“有志青年”与北京、与农村组、与“紫阳万里”那个标示着中国前途的“体制内改革派”的联络站。
老何家的卫生间和封闭阳台改装的放一把折叠床简易客房,就是我们从各地来拜山门“找组织”的游侠们的常备旅店,常来常往,都与老何亲如兄弟。农村组和后来体改所的诸多大将,好几位是在老何家认识的。那天老陈和老何说什么事,我到的时候他刚要走,匆匆寒暄一下就离去了,给我留下个自来熟的山寨大哥印象。事后跟老何说,我今天电梯里遇见了个陈永贵大叔(也住那楼里),又见了你们农村组的老大也姓陈,都跟农村关系很大啊。这次来就是谈我们省里的一伙兄弟们成立省农村发展组的事的!
后来再见老陈,就是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中了,常常是他在台上口如悬河,滔滔高论,我们在台下忙着笔记要点,要么存疑待辨,要么心领神会。当然会下也常有一干人马与他席地而坐而纵论天下的时候,不同观点辨得不可开交。当时的口号叫“老青对话”,“老”就是中共高层有感觉需要改弦易辙的几位开明派老人,“青”就是我们一帮不怕鬼不信神的愣头青。当时没有“愤青”这个词。自从魏京生在十多年前在西单墙上喊出了“呼唤第五个现代化”之后,倾其一己之全力参与推动中国的改变,已经是我的有头脑的一代同龄人的基本共识,所以要贴标签的话,我们是一批“改青”,而老陈就是这批“改青”的头。而今“改青”们有的流亡了,有的学乖了,更多的是交了投名状,从既得利益集团处分了一杯甚至一桶羹了。坚持着青年时代理想和独立人格的,已经寥寥无几。不知新一代青年们,还有没有人能反抗洗脑,思想越狱,认清世界潮流,继续为中国治病的大业?
老陈这个头是“动手派”的头,身体力行,爬山涉水搞调研找发展出路的一派。 还有一大类也同样重要的“动嘴派”,写文章出书办讲座为主的“改青”,金观涛算是头。当时“四大青年思想领袖”,即金观涛、方励之、李泽厚、温元凯,加上《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包遵信,属于思想理论上的先行者,而陈一谘,我们当时叫他谘先生,和当时的另外四位“改革四君子”,朱嘉明、黄江南、翁永曦、王岐山,属于行动上的先行者。在中共的前30年残酷愚昧统治开始解冻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十个名字像暗夜里的微弱火炬。 哪位有心人把这十位名人后来各自的命运故事汇编成书的话,会是一本未来的国史好教材。当年北京有位作家柯云路,实际上是俩口子联合的笔名,写了《新星》《夜与昼》《衰与荣》三部曲改革系列小说,把这一伙人改名换姓统统写了进去,可算是那段历史的一段引言吧。
“动嘴派”和“动手派”两大路“改青”大侠们,一共有过两次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84年9月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我当时忙于其他的项目,没有时间写论文参加代表竞选,我所在的省有两位兄弟赴会。那个会是“老青对话”的一次大动作。那一年,“农村组”升级,体改所正式组建,老陈担重任,通过鲍彤,与赵紫阳热线连接。来自“改青”们的活跃思想创新与来自中国统治中枢的现实问题有了沟通探讨的渠道,中国进入了自五四后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短暂良性发展区。
第二次是1989年4月的“改革十年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会议”,在丰台的京丰宾馆召开,史称“京丰会议”,这时我已经从美国作访问学者归来,和我们省里另外的六位“改青”一起参加了,全国共400多人。这次会议是在改革遭受巨大阻力、“三李倒赵”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召开的,赵紫阳提出“究竟如何在三五年内走出改革困境”是会议的主题。而我们一到场,感受到的是“改革即将失败”的悲壮气氛。据说体改所的成员因为没日没夜地拼命赶工,三分之二的老婆提出离婚了,三分之一累得得了肺结核,正当中青年的白南生居然满头头发已经花白,一见面吓了我们一大跳。三年前我们接待他和周其仁来云南调研时,头发还是全黑的啊。其他大侠们也是个个满脸憔悴。
虽然我们无人信迷信,但是事后有人总结说,这个会标示着中国又一次恶运的开始:首先,老陈平地走在地毯上居然摔了一跤,把腿摔坏了!其次,温元凯的长篇报告数数居然说了13点21条,净是不吉利的坏数字,居然还提出了请共产党向人民承认过去的错误以重新上路的说法,真是书生啊。会议开幕是4月1日,是愚人节。闭幕是4月5日,是鬼节!10天之后,胡耀邦不幸去世。悼念的学生们开始向天安门广场集聚。中国历史的车轮由此又滚向了两个月后的血腥。4月18日,白南风作了两个大气球运到广场,一个写着“耀邦不死”的飞上了天,另一个“改革万岁”的却破掉了。老陈自己说,不祥的预感由那时开始了。“体制内改革”之梦开始破碎。5月15日,体改所被内定为“反革命组织”。19日,老陈主持起草了《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理念上与那个统治体制决裂了。5月28日,鲍彤被抓。5月30日,何维凌在绝食学生与邓家之间的奔走斡旋不成后被抓。6 月4日凌晨三时,枪声中,老陈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走上逃亡之路。
老陈自己回忆,他辗转躲藏追捕,与7月5日成功离开了中国。我和前妻则是6月19日中午,在6月20日凌晨所有护照无效之前半天,在满洲里火车站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离开中国的。阴错阳差,我们随身带着省政府批发的“出国任务批件”,因为7月份在欧洲要参加两个学术会议,出事前很早我们就办理好了护照签证。所以老陈是“逃亡”而我和前妻是“违反外事纪律出国不归”,共党定出的“出走性质”虽不同,同是不归路。当气笛长鸣,火车徐徐离开中国国境时,我写下“曾悴心力扶社稷,怒见昏君屠鸣犊……拂袖一去八万里,狂飙送我隐天涯……”可能也是老陈当时的心情吧。
再见老陈,是那年10月在我母校召开的《八九民运与中国前途讨论会》上。老陈又恢复了他一贯的乐观自信的架势。“我跟共产党没有仇,”他大大咧例地说, “九个常委里也就是李鹏这个大坏人要整我”。改革十年风云的一代天骄,“改革操盘手”,已经在逃亡之中,却还没有放弃对那个政权的幻想,真令人扼腕长叹!老陈后来组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参与又退出民运,隔三叉五的弄个什么研讨会等等,以及有一年折腾动员了我们许多海外学者一起搞大会战式的“中国发展总体研究报告”,都是赤子之心不悔,而上奏折之习未脱啊。
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走向发展,我经过多年的反思与研究,已有的另外的看法,但是每当老陈发声召唤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时,我还是尽力而为的,不为别的,只为了过去共有的梦。 有位名气很大的哲人曾说过,“我們不能用制造问题时的同一水平思維來解决问题。”老陈晚年的遗憾是,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不同类型的坎坷(我相信这本纪念文集的其他作者已经有太多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了),他竟然没能完成思维规范的越狱,他的思考方式、立足点、方法论,仍然深深地打着那个体制和那个文化的烙印,令人扼腕长叹! 老陈你别瞪眼,我是实话实说。
斗转星移,乾坤穿越。最后一次和女友专程开车去LA看他,是2011年某月。一代英雄已垂垂老矣,但锐气一点不减当年。虽然医生早有警告他来日无多,他还是一惯乐观地相信某些中医会带给他带来奇迹。为了把对他的日常作息养病的干扰减到最小限度,我们电话上说好只谈一个小时的。结果他一开口就收不住,一转眼已经和我们谈了两个半小时,话题绕来绕去,还是离不开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前途。我们好几次想打断他而告辞,他却说“我两年闭门谢客养病,你可是第一个访客哪,我开戒了啊。”说高兴了,居然要了烟来抽起来,我们和他家人一起拦也拦不住。“我忘了你今年多大”,他问。我说“五十多了吧”。“啊,太年轻了,以后要当重任”,他坚信不移地说。
真的么,老陈?
前不久与远在台湾讲学的朱嘉明兄通了个电话,也说到年龄。嘉明说,我都过六十了,你多大?我说我57年生人啊。嘉明在电话那边叫起来说,哈哈原来你是个小年轻啊!
老陈74岁走的,正好是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如此算来,我可不还得辛苦20年。希望在这20年里,我们前前后后一代人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目标--找出中国病的病根予以根治,找出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的道路,能够有所实现。
每个人都是要离开此世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得了不治之绝症的。唯一的差别只是个时间的早晚而已。老陈你先走一步,一路走好。兄弟我再折腾点有意义的事,待再见你时好和你有得吹嘘摆乎的。
2014底成稿
剑申鹄,独立学者。八十年代参与中国青年改革者团伙,其中赴美做访问学者两年。六四后出走美国,1995年获组织管理学博士。曾任助理教授(加州州立大学)、讲师(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讲师(北大、清华)、创业者、跨国教育公司高管、团队培训师等职,现居亚历桑那州专事写作。